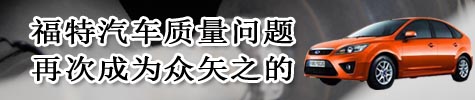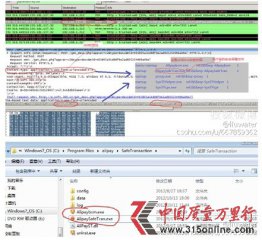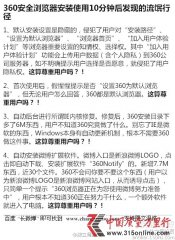但施正文認為,郵政普遍服務目前主要由公有制郵政企業來提供,但這并不代表民營的快遞公司就沒有承擔郵政普遍服務的責任。首先,快遞公司以納稅的方式已經承擔了義務;其次,現在快遞已基本覆蓋了城市,成為城市居民郵政普遍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說它們完全沒有承擔這方面的責任也是不全面的。
此外,施正文認為,開征這項基金,與當前財稅體制改革的大方向相背離。首先不符合結構性減稅的原則,該基金按件征收,名義上是基金,實質上就是對企業利潤征收的稅。其次,當前財稅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是要重稅輕費,以政府性基金和收費為主的非稅收入比例已經太高了,不宜再開征新的基金。
“一旦以行政手段建立一個基金,這個基金就會成為一個自我封閉的循環。雖然納入了預算,但基金預算是相對獨立的,規范性、透明性、公開性都是不夠的,會增加監督的環節和成本。”施正文說,“基金征收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業務,需要了解政策法規等,這對于郵政管理機構的人員素質也是一個考驗。”
在施正文看來,《郵政法》所說的基金,不一定非要指額外征收的基金,也可以是以財政撥款建立的基金,只是財政支出的一種形式,后者也符合財政學上對基金的定義,在實踐中也有價格調節基金等先例。
郵政普遍服務該誰埋單
民營快遞領域,風波再起。本報今天對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的征求意見稿做了報道。按照“征求意見稿”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按照該辦法規定繳納郵政普遍服務基金。
這意味著,一定規模以上的民營快遞企業,將為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做出貢獻。這個基金,是謀求對郵政公司的信函遞送等普遍服務部分的運營進行補貼。 在一些“老少邊窮”地區,信函遞送等運營比較困難,遞送價格可能低于實際運營成本。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的征收,主要是補貼于這部分業務。
問題就出來了:其一,郵政普遍服務該不該得到補貼;其二,誰該為這份補貼埋單?
回答第一個問題的前提,是郵政普遍服務究竟是處于怎樣一個狀況。贏利還是虧損,需要由數字來說話。倘若事實并不像大家所以為的那樣,并非真的很困難,而只是“叫”得困難,則不該補。倘若有虧損,則必須補。
有一個理念是明晰的:無論郵政領域怎么改革,無論這個市場的利益怎么分配,“老少邊窮”地區的民眾不能失去基本的郵政服務。從這個角度說,無論是誰,總要有人對此普遍服務做出貢獻。
問題在于,誰該為這份補貼埋單?這就是第二個問題了。埋單的候選人有三:一是郵政公司自身,通過在其他業務領域的收入補貼虧損部分;二是進入快遞業務市場的其他類型企業為此埋單;三是政府通盤考慮,由公共財政支付。
就目前情況來看,郵政公司顯然不愿意單獨為之付出代價。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的征收,指向了“境內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這就必然給符合繳納基金的一定規模以上的快遞企業增添負擔,也必然會引來這些企業的反彈。
那么,民營快遞企業該不該從市場所得中,拿出一部分資金?有行業人士曾這樣反駁:這個普遍服務基金又不能為我們服務,我們憑什么拿錢出來?而 “征求意見稿”之所以向民營快遞企業群體伸手,一個基本的邏輯應是,這批企業進入了原先郵政系統中能夠賺錢的領域,卻把無錢可賺的部分丟給了郵政公司。
民營快遞企業該否再掏錢,涉及一個公正性問題。這些企業已經納稅,再為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埋單,是否有雙重繳納的嫌疑?這個追問不可忽視。如果非要該群體再掏出一筆,本質是讓他們交市場準入費——誰讓他們進入了一個原先由國有企業專營的領域了呢?
市場準入費的支出當然值得商榷。這個市場如果不開放,則當前的整個市場狀況大家很清楚。回到低效率的時代,不符合這個社會的總體利益。更要厘清 的是,如果一定規模以上的民營快遞企業承擔了這筆開支,則一定會導致整體運營成本的上升——實際上,最后必然是由民營快遞業務的消費者為此埋單。而消費 者,無論如何沒有理由再增加一筆支出。
因此,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的征收對象,應該排除民營快遞企業。這筆資金意圖補貼郵政企業,先得看看被補貼者是否真的需要被補貼。郵政企業同樣也在“有油水”的市場中參與競爭,讓其他競爭對手補貼其普遍服務部分,總讓人感到有些不合常理。至少,市場的邏輯顯得較為模糊。
在我們看來,如果數據表明郵政企業確應得到補貼,則更為合宜的出資者是公共財政。道理很簡單,“老少邊窮”地區民眾的郵政服務,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準公共服務。既如此,以公共財政進行貼補,更顯得名正言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