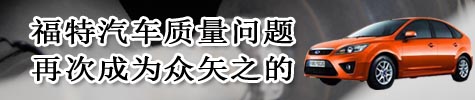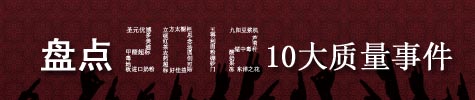【老槍/文】年年春運年年罵,今天又多了一個罵點:搶票插件。
對媒體言,每年春運都是一個可以用最廉價方式獲取更多注意力的良機。只要走民粹路線,就可以輕而易舉獲得喝彩。微博時代,連黨報國社也不例外,且民粹的比市場化媒體還粹。
這個周末,搶票插件正被議論的如火如荼時,黨報——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在周六的每晚例安中寫道:
【你好,明天】當搶票插件引發熱議,誰又理解農民工的鄉愁?他們在寒風中排起長隊,票源卻在網上瞬間搶購一空,高科技竟成剝奪機會的推手。給售票窗口留些車票,這么簡單的方案難道想不到?關愛弱勢群體,不止于廉價的同情,更在于公平的制度設計。機會公平,階層才不至固化,社會才能存續希望。安。
但國社——新華社顯然不能同意。周日,財經網微博發布的一則新華社記者述評如是說:
【新華社:鐵道部工信部不能“自己傻就怨別人太聰明”】鐵道部斥資3億建起的平臺竟經不起住小小網絡插件沖擊!自己不好好修補Bug,卻忙于“約談”和“叫停”,動用行政權力阻止市場行為。“一票難求”是旺盛需求與運力不足間的矛盾。搶票軟件出現說明,有市場就擋不住有研發來填補。
一方為不會使“高科技”的農民工們仗義,一方為會用“高科技”的小白領們直言,雙方背后都站立著足夠龐大的群體。而且,事實上,這兩者現在都是這個社會中的屌絲群體,越來越談不上誰比誰更有地位更強勢了。如果由此引發一場“戰爭”,那將是一場中國社會兩大屌絲群體的大對決。這恰是中國社會當前的荒誕真實。
相比較而言,國社比黨報更接些地氣,點出了市場供求這個要害。
但一說到市場供求,就有另一批牛人登場,他們自以為挾經濟學利器,可平息天下一切紛擾繁雜:價格決定論。所謂“春運”,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造之。只要漲價,漲到供求平衡,什么叫“春運”?根本不存在!
只是,若按他們這套辦,那最有回家心理與情感需求的農民工和小白領們,需求將得不到滿足。而相對富裕者,則可以乘經濟學長風母慈子孝天倫得圓。春節的城市,留給住工棚的民工和擠住出租屋的小白領這兩大屌絲群體共享,也算是經濟學帶給屌絲們的福利。或者,干脆,把這類牛人稱之為中國式福利經濟學家。
回到問題本源。
無論非實名制下的排隊購票黃牛倒票,還是實名制下的網絡刷票插件搶票,所有的票,最終是有人用來坐了車。這些年來無論鐵路、公路、航空,整體運力在快速增長,但春運的壓力卻沒有得到有效緩解。歸根到底是人口流動增得更快。
春運有解嗎?
鐵路官員說,除非儲存平時正常運力的10倍,否則無解。
我們可以在經濟上建設并承受這樣一個運力系統嗎:一年中的11個月只用10%能力,只春運這一個月用足?
顯然不能。
反過來,我們可以讓人口在這一個月中的流動降低90%嗎?
顯然不能。
那么,我們可以讓這一個月里需要回家的人中的10%最富裕者滿足需求,而把另90%的需求用價格門檻擋回去,讓他們在春節這個情感特殊窗口期回不了家嗎?
這不是個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個敢不敢的問題:誰敢?
都不能,或不敢,那就無解。
要面對這個現實,在此前提下,盡量從方方面面把平衡工作做的更好些,所謂田螺殼中做道場。在這個問題上,民粹也好,經濟學也罷,作為平衡社會心理的“罵器”,用用無妨,但要適可而止。
無解的春運問題,事實上是中國現行模式繼續下去終將走入無解困境的先兆與縮影,更是警訊。
為什么會有春運問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答案是現成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所致。
那么,再問: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怎么造成的?有解嗎?
這個問題,本槍在今年的“準元旦獻詞”《進退改都難的時代》一文中已做過回答:
“中國的發展模式實質被決定于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模式。以中央為總核心,圍繞著總核心,是省級子核心;圍繞著省級子核心,是地市級子子核心;圍繞著地市級子核心,是縣級子子子核心。四級核心層次分明層級清晰,方向更清晰:統統以上級核心為中心點向上而指。
這一模式造成了所有資源被最大限度地為上級核心所在地吸納。這四級核心城市與區域把幾乎所有資源全部吸納到極限,而又無力對所有隨資源吸納來的人群做相應平等公共保障。同時,更使得廣大的四級核心之外的地區,因為把連人在內的資源都吸納殆盡,而無法擺脫貧困得到發展。”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的權力結構模式不作根本改革與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就無解。由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的春運問題,也就當然不會有解。
更進一步的事實則是,中國的更大發展不平衡是社會整體的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不平衡,是由權力模式導致的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結果,而非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原因。這種結果的日益嚴峻,又反過來促使社會發展愈加不平衡。包括春運在內的所有由此所致的問題,也就更加趨于無解。
中國社會不平衡的特征是,權力核心所在之地實質上就不是現代社會,而離權力核心越遠,離現代社會就更加遙遠。在遠離權力核心的地方,人們不僅嚴重缺乏最基本的生存與發展機會,更缺乏最基本的精神自我生存土壤。因此,人們不得不逃離那些遠離權力核心的地方,流向各級權力核心所在。這既是尋求更高收入的必須,也是尋求更多精神慰籍的必須。但,殘酷的現實卻是,這些權力核心的本質是吸血而非納新,這就使得絕大多數人成了所謂流動人口,在物質與精神上,都不得不以家鄉為巢穴以工作地為就食所,如候鳥般來回“流動”。
這種不平衡的實質是中國一直把自己綁定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遲遲無法進入一個權力逐次自治的公民社會。因此,一個14億人口之巨的國家,無法形成多中心的相對權力完整而自洽的自治區域群,使得人們在各自所居區域,都能有機會得到雖然作橫向區域比較有差異甚至是較大差異,但卻在區域內相對完整的自我發展可能。
理解這一點必須理解兩件事:
一、多中心的、權力逐次自治的公民社會不是否定城市化。
二、人們的自我發展需求并非只有物質需求。在物質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后,對社會事務的表達與參與需求同樣重要。
權力集中的體制與模式,在30余年來,看似造就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說“看似”,是因為雖然有人不同意快速發展得益于權力集中,卻也無法否定,因為歷史無法重試。但可以通過觀察如春運、如異地高考等等無解、難解問題而預言的是:
這種權力集中體制與模式的紅利已越來越到盡頭,繼續堅持與強化下去,很可能將走向反面。漸進多元權力中心與公民社會培育發展,對使社會可持續發展來說,越來越成為必要與必須,也越來越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