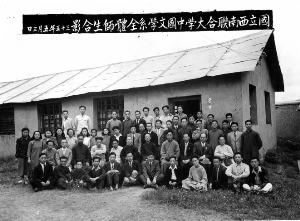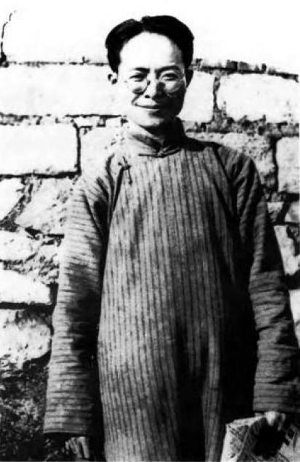四院鳥瞰圖,當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檔案館提供)。 西南聯大中文系1946年師生合影(北大檔案館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1957年畢業合影(楊鑄提供)。 沈從文在昆明(1938年,選自《沈從文全集》)。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為中國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標志著中國語言文學開始形成現代的獨立的學科。中文百年變遷,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創辦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錢少 新京報:1910年3月31日京師大學堂成立的“中國文學門”,是我國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現代大學的學科中,法學、醫學和神學是三大最古老的學科,那么中國現代大學創建中文學科的初衷是什么? 陳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開始并沒把“中國語言文學”作為相關訴求。時人普遍貶考據、辭章、帖括為“舊學”,尊格致、制造、政法為“新學”,教育改革的重點在“廢虛文”而“興實學”。 新京報:可“文學教育”最終還是進入了改革者的視野,為什么? 陳平原:因為不管是舉人梁啟超,還是大臣張百熙、張之洞,一旦需要為新式學堂(包括大學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據當時的譯介略加增刪。而西人的學堂章程,即便千差萬別,不可能沒有“文學”一科。于是,不被時賢看好的文學教育,由于大學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報:有點陰差陽錯的味道。 陳平原:對比晚清三部大學堂章程,不難感覺到文學教育的逐漸浮出。1898年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開列十種“溥通學”,十種“專門學”。前者“凡學生皆當通習者也”,故有“文學第九”之列;后者培養朝廷亟須的專門人才,故只有算學、格致學、政治學(法律學歸此門)、地理學(測繪學歸此門)、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醫學歸此門)。也就是說,“文學”可以作為個人修養,但不可能成為“專門學”。 新京報:問題在于“文學”還是成了一門“專門學”。 陳平原:因為在1902年,張百熙奉旨復辦因庚子事變毀壞的大學堂,并“上溯古制,參考列邦”,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此章程對“功課”的設計,比戊戌年間梁啟超所代擬的詳備多了,分政治、文學、格致、農學、工藝、商務、醫術七科。文學科又有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等細目。將“詞章學”列為大學堂的重要課程,不再將其排除在“專門學”之外,總算是一大進步。 新京報:是什么原因讓“文學”從“專門學”變成了一門重要學科? 陳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內設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等八個分科大學堂(接近歐美大學里的“學院”)。 其中,文學科大學分九門:中國史學、萬國史學、中外地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國文學等。不用說,后五者純屬虛擬。與中國文學門從課程安排、參考書目到“文學研究法”都有詳盡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這五個文學專門,均只有不著邊際的寥寥數語。單有設想不行,還得有合格的教師、學生、校舍以及教學資料。1910年京師大學堂各分科大學正式成立,其中有虛有實;中國文學門之所以步履比較堅實,不是因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為我們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錢較少。 學科初衷 擔心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失落 新京報:當時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陳平原: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這很難說。到底是根據“上諭”、“章程”,還是主持其事者的論述?一定要說,我推薦張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參酌變通”的指導思想,在同時上呈的《學務綱要》中有詳細解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著稱的張之洞,強調“中國文辭”不可廢棄,與其說是出于對文學的興趣,不如說是擔心“西學東漸”的大潮過于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 新京報:經過一百年的發展,目前的中文學科體系是否完善,與初衷是否一致? 陳平原:歷經百年的演進,中國文化依舊屹立,而且時有創新,并沒有因西學輸入而失落,這點很讓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雖說以我為主(這是學科性質決定的),但從一開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學史”、“外國科學史”、“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的課程設計。 至于學科體系,不用說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學校課程表的水平。 新京報:能否舉例說明一下? 陳平原:我曾舉過一個例子,1915—1916年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課程總共有九門:中國文學史、詞章學、西國文學史、文學研究法、文字學、哲學概論、中國史、世界史、外國文;而2009—2010學年第二學期北大中文系開設的研究生課程,總共是57門。課程并非越多越好,我們正在自我評估;但這起碼說明一點,所謂“學科體系”,不可能一成不變。 新京報: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大學里的中文系都“升級”為學院,包括專業設置也不統一。 陳平原:今天中國大學里,很少有像我們這樣依舊還叫“中文系”的,絕大多數都升格為“文學院”或“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了。這是自我定位的問題,無所謂好壞。之所以選擇相對保守的路徑,與我們定位于精英教育有關,本科生80%進入中外各大學的研究院繼續深造,不適合做“短平快”的設計。 中文價值 要產生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 新京報:中文學科這一百年,最大的啟示是什么? 陳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將我們的中文系跟國外著名大學的東亞系比,人家是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我們是本國語言文學研究,責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樣。 作為本國語言文學的教學及研究機構,北大中文系的獨特之處在于:我們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有效地介入了整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溢出效應”。也就是說,我們的教師和學生,不僅僅研究本專業的知識,還關注社會、人生、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與整個國家的歷史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這個傳統,在我看來,永遠不能丟。 新京報:這一觀點基于什么考慮? 陳平原:我們要出容易獲得承認的學科體系內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認的跨學科著述,還希望出不怎么“學術”但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這就需要一種開闊的視野以及從容淡定的心態。 新京報:恕我直言,現在這種心態已經是非常罕見了,是不是有點理想化? 陳平原:我承認,這一追求,跟目前的評估體系不太吻合,會有很多遺憾。到底是“快馬加鞭”好,還是鼓勵“十年磨一劍”,我相信老大學的著名院系都面臨這個問題。 當領導的,頂住壓力,給老師們創造盡可能寬松的學術環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認同這一理念,且自覺地奮發圖強。若不是這樣,外無評估的壓力,內無奮斗的動力,回到吃大鍋飯的時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學問”,那也很危險。 新京報:一直以來,社會上包括高校內都以“萬金油”來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嗎? 陳平原:稱中文學科為“萬金油”,大概是指其適應面廣,專業性不強。這大體屬實,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學生就算“知識分子”;現在呢?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大學生毛入學率(即同齡人中能夠上大學的人口),1998年是10%,現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標,2020年達到40%。這種狀態下,我們反省本科教育的專業化程度到底應該多高。 在我看來,有些技術性的活,崗前培訓就行了,根本用不著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學問,到研究院再學,一點都不遲。像中國這樣,高中就開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階段就設商學院、法學院,我以為是不妥的。 新京報:你認為大學應該怎么學? 陳平原:大學四年,能獲得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加上很好的思維訓練,這就夠了。 問題在于,在中國,大部分人還是把“上大學”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學和自己日后所從事的職業沒有直接對應聯系(現在已經有這種趨勢,盡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會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會,了解人類,學點文學,學點歷史,陶冶情操,養成人格,遠比過早地進入職業培訓,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這樣來看中文系、數學系等基礎性學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階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報:有數據表明,現在每年報考中文的學生逐年呈下降趨勢,報考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嗎?是中文系科的問題,還是社會發展的問題? 陳平原:這個問題本不想多說,你既然追問,我如實匯報:托北大這塊金字招牌的福,我們的本科招生情況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沒有擴招,一直穩定在80至100人,視每年考生水平而略為上下浮動。今年情況尤其好,最后錄取了106人。本來我們在京計劃招收5人,可錄取線上共有27人報考,最終錄取了13人。 社會認知 要相對脫離一時一地的就業市場 新京報:學科就業率應該也算是學生報考時的一個重要參考。溫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說,“文氣”應該是中文系學生的強項。您認為“文氣”是中文學科的優勢所在嗎,為什么?相對于其他學科,中文系畢業生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 陳平原:中文系學生的競爭力,用一句話說,那就是“厚積薄發”。因我們的課程設計全面,注重基礎訓練,要求同學潛心讀書,避免過早介入實務層面。因此,一旦進入實際工作,上手也許不是最快,但后勁肯定很足,發展前景比較廣闊。 當然,正如溫儒敏教授說的,“會寫文章”也是中文系學生的一大特長。只是這里所說的“文章”,包括文學創作,也包括學術論文,還有一般性寫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生80%進了研究院,故對學術論文的強調更多一點。 新京報:作為中文系主任,您怎么看待和解決中文系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換句話說,一個高中生在高考后,面臨著多個學科的選擇,您認為最值得他選擇中文系的理由是什么? 陳平原:六年前我寫過《我看“大學生就業難”》,大意是說,大學擴招,專家們大都主張應注意專業對口。這一點,我不無疑慮。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訓練為中心,這樣的學校容易與就業市場對上口;可又講提高學術水準,又提瞄準市場需要,這“口”到底該怎么“對”? 在我看來,與其在研究型大學里增設許多實用專業,弄得不倫不類,還不如放手一搏,相對脫離一時一地的就業市場。這里的基本假設是:社會需求瞬息萬變,大學根本無法有效控制;專業設置過于追隨市場,很容易變成明日黃花。學得姿勢優美的屠龍術,沒有用武之地,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強身健體。 新京報:現在,這個“預言”真的實現了。 陳平原:對。2010年5月5日《文匯報》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熱門”專業風光不再》,說根據調查,十個失業率最高的專業包括工商管理、計算機、法學、英語、國際經濟與貿易等“熱門專業”。 在我看來,中文系這樣的長線專業,沒有大紅大紫,也不會大起大落。并非北大情況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國重點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會上,我問了一下,大家都有這個感覺。 新京報:我們還是以招生為例來談談吧。 陳平原: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學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長都希望孩子念能賺大錢的院系,中文系風光不再。可最近幾年,情況又有變化,開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報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們總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內蒙古、云南),讓很多人跌破眼鏡。 新京報: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說的“狀元”? 陳平原:不是說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個象征意義,代表社會上開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績頂尖而愿意選擇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報:為什么? 陳平原:一是視野比較開闊,二是家庭相對富裕,故更多地考慮個人興趣而不是就業前景。 因此,我有個大膽判斷:隨著中國人日漸“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學科,開始“觸底反彈”了。 所謂大師 “大師”要甘冒被邊緣化的危險 新京報:清華的老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之大在大師之大。北大中文系歷史上出現了不少知名的大師,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師”,估計會有不少人懷疑。 陳平原:不做詞語溯源,今人所說的“大師”,主要是指在某一專業領域做出突出貢獻,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當然,因時、因地、因論述框架的差異,“大師”的標準不一樣。 比如,為了紀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們推出“北大中文文庫”,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現已去世的名教授,編纂適合于大學生/研究生閱讀的“文選”,讓其與年輕一輩展開持久且深入的“對話”。開列名單時,以1952年院系調整為界,前面是姚永樸、黃節、魯迅、劉師培、吳梅、周作人、黃侃、錢玄同、沈兼士、劉文典、楊振聲、胡適、劉半農、廢名、孫楷第、羅常培、俞平伯、羅庸、唐蘭、沈從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后面則是游國恩、楊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驊、岑麒祥、浦江清、吳組緗、林庚、高名凱、季鎮淮、王瑤、周祖謨、陰法魯、朱德熙、林燾、陳貽焮、徐通鏘、金開誠、褚斌杰。 具體操作時,碰到很大困難,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后二十種;好在前二十位聲名顯赫,業績廣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場,他們就是我們敬仰的“大師”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學術史視野,他們中有的依舊是“大師”,有的則稱不上。 新京報:您認為是“大師”的標準變了,還是時代不需要“大師”,或者我們這個時代很難產生“大師”? 陳平原:我們這個時代能否產生“大師”?這一追問本身,隱含著某種批評。短期內,人類智商不會發生突變,沒人規定“大師”只能出在哪個時代。但回顧歷史,有時天才成批涌現,讓你目不暇接;有時又十分沉悶,即便那些被捧為“大師”的,也都不夠精彩。這里有外在環境的限制,也跟整個思想/文化/學術潮流的演進有關,強求不得。 當今中國社會,風氣浮躁,“大師”的帽子滿天飛;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氣,別整天記掛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為“大師”(那樣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邊緣化的危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劍”,出大成果,做大貢獻。明白什么是學術的最高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新京報:在歷史上,某種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識分子”的同義詞,但是,今天二者的關系似乎愈發疏遠。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識與責任擔當發生了變化嗎? 陳平原:你這么說,未免太抬舉中文系了。雖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國,社會科學比人文學科發展得好;影響國計民生以及政府決策的,是經濟學家、法學家,而不是哲學教授、文學教授。 中文系師生會寫文章,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更多的是體現“位卑未敢忘憂國”。有“責任”,有“擔當”,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報:以北大為例呢? 陳平原:具體到現在的北大中文系師生,或許沒有當初的思想活躍,因其大都轉入專業研究。這是整個社會環境決定的,不能怨老師或學生。“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依舊是很多人的夢想———能實現多少,那是另一個問題。 母語教育 “大學語文”有必要成為“必修課” 新京報:現在社會上出現了“國學熱”,比如北大就有各種各樣的“國學研修班”;出現了“漢語熱”,比如不少外國人熱衷學習漢語;還出現了“漢學熱”,比如海外漢學家受到熱捧等,在這種背景下為何會出現“中文冷”(主要是指報考和就業)? 陳平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有點纏繞。“國學熱”、“漢語熱”、“漢學熱”以及“研修班”不在一個層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學術風氣,有的則是經營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討論。上面已經說了,“中文”并不冷,所謂中文系的招生與就業“有問題”,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誤解。 新京報:與其他國家相比,您認為我們的“母語教育”是重視過度還是不夠重視? 陳平原:這個問題問得好。怎樣進行“母語教育”,確實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我在大陸、臺灣、香港的大學都教過書,深感大陸學生的漢語水平不盡如人意。普遍有才氣,但根底不扎實,這恐怕跟我們整個教育思路有關。 新京報:產生這種差距的原因在哪兒? 陳平原: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國教育,中學沒有文理分科一說,所有大學生都得上“大一國文”。這個制度,臺灣堅持下來了。而大陸呢,高中實行文理分科,大學又沒有強制性的中國語言文學教育。 記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幾個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來,說現在的學生中文不好,影響其日后的長遠發展。于是,請中文系為全校開設“大學語文”。可這個制度,在一次次的課程改革中被逐漸消磨掉了。因為,必修課時有限,每個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專業課。政治課不敢減,“大學語文”又不是教育部規定的,就看各院系領導的趣味了。 新京報: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學里推廣“通識教育”掀起了熱潮,現在似乎冷了下來。 陳平原:我記得華中理工大學(現改名華中科技大學)在校長楊叔子的強力主導下,1994年春創辦了系列“人文講座”,第二年秋天又組織全校新生參加“中國語文水平測試”,且規定“過了語文關,方可拿文憑”。不知道后來情況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質教育”,也有模仿國外大學做“通識教育”的,這些都很好。 只是“素質教育”面很廣,且容易演變成“營養學分”。在我看來,針對目前社會上對于母語的忽視,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確實有必要在大學里設置類似“公共英語”那樣必修的“大學語文”。 新京報:曾有人提出,漢語沒有針對公民語文基本能力的標準,所以學生們都把精力放在學習可以標準化檢測的外語上,母語教學需要這個標準嗎? 陳平原:我不贊成對公民進行語文基本能力的測試。設想每個中國人都懷揣一本“漢語十級”證書,那不很好笑?關鍵是如何提高大家學習中國語言文學的自覺性。 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 以上圖片均選自溫儒敏主編《北大中文系百年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